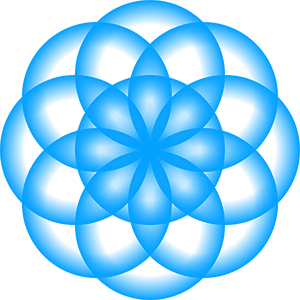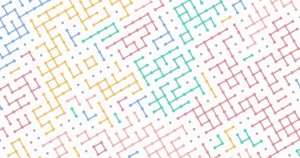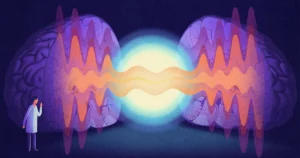介绍
In 卡桑德拉·埃克斯塔沃尔哈佛大学的办公室挂着一张标语牌,上面画着彩虹旗和友好的邀请。
“欢迎您来到这里,”上面写着。
“我之所以把它提出来,是因为我认为让人们看到你的身份很重要,尤其是当这些身份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时,”进化遗传学家 Extavour 解释道,她于 2014 年成为第一位获得哈佛大学生物科学终身教职的黑人女性艺术与科学学院。
埃克斯塔沃尔本人在职业和个人方面都具有多重身份,足以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文艺复兴女性。她是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一位受过古典训练的女高音,与波士顿地标管弦乐团以及亨德尔和海顿协会合作演出。
除了教学和歌唱之外,Extavour 还研究地球上最早生命的生物化学和遗传学。她想知道第一个细胞是如何发育并最终进化成多细胞生物的。什么细胞机制 让复杂的生活成为可能?她问。更具体地说,生殖细胞(产生卵子或精子,将遗传信息从父母传递给后代)对多细胞生命的发育有什么特殊影响?
她的实验室工作结合了实验和高等数学,赢得了进化生物学家的广泛关注。
在她的2000年 博士论文Extavour 表明,生殖细胞会竞争将信息传递给下一代的机会。在 她在哈佛大学的实验室她证明,细菌在创造基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基因对于在更大、更复杂的生命中建立生殖细胞系至关重要。最近,在研究昆虫的卵时,Extavour 和她的团队推翻了人们普遍持有的关于细胞形状多样性的驱动因素的假设。
“我对地球上多细胞生命的起源非常好奇,”埃克斯塔沃尔最近在她位于剑桥的办公室接受 Zoom 采访时解释道。 “我知道我永远不会看到它。但我对此想了很多。”
广达 深秋时节,我们在三个不同的采访中与她进行了交谈。为了清晰起见,采访内容已经过精简和编辑。
介绍
由于您的研究重点在于开始,所以让我们从您的开始。你在哪儿长大的?
多伦多,当时是工人阶级社区,称为“Annex”。这里几乎全部被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家庭占据。
您是那些一直知道自己长大后想成为一名科学家的孩子之一吗?
不,我想象我会成为一名音乐家。或者也许是一名舞者。我从四岁起就开始打钢鼓。我很小的时候就可以识谱。我在小学时就开始学习管乐器。后来我又学了声乐。
我的童年有很多音乐。我的父亲是来自特立尼达的移民,他在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担任技术人员养家糊口。但他也是一位职业音乐家。他定期举办音乐会。我和他一起表演。
在家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们可以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无论是掌握一种新乐器还是进入镇上最好的高中。如果我表达对某件事感兴趣,得到的回应是:“去图书馆,了解有关它的一切并制定计划。”
你的家庭听起来很了不起。
我们的家族故事是这样的:我们出身卑微,但却才华横溢、坚强有力、富有创造力。
我们从小就被认为是与众不同的、特别的,但其他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父母教导我们:“世界不会总是因为你是谁而重视你。不要让它阻止你过上最好的生活。”
在 1970 世纪 XNUMX 年代的加拿大,在一个跨种族家庭中长大是否具有挑战性?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明白很多人不喜欢我父亲是黑人而我母亲是白人这一事实。我母亲的家人对她嫁给了一个黑人并生了四个黑人孩子并不感到兴奋。他们花了一些时间才接受它。
回想起来,我逐渐意识到我们家庭的外在给了我很多有用的工具。例如,我从小就知道外界可能对我有敌意,所以我不能指望它得到准确的反馈。我在早期就自己决定某件事是好是坏,或者是有趣进行了很多练习。当您设计实验时,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介绍
鉴于您很早就对表演产生了兴趣,那么对遗传学的兴趣是如何进入您的生活的呢?
完全是偶然。在多伦多大学上大学的第一年,我发现自己很快就需要选择专业。当时我正在合唱,我问坐在我旁边的邻居她的是什么。 “遗传学,”她说。这完全是一个随机的决定。
但幸运的是?
是的。因为遗传学专业要求选修生物化学。我以前上过生物课,但我发现它们——至少是它们的教学方式——是一个需要记忆的不连贯的清单。
另一方面,生物化学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逻辑难题。有所有这些不同的部分——蛋白质、线粒体、基因——它们一起工作,形成一个可以做事的细胞。这个游戏的目的是弄清楚各个部分如何协同工作。我发现这非常吸引人。
现在,我还没有在学术环境中长大。我对研究职业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我今天的工作是否存在。
但我询问了学校,一位年龄较大的学生告诉我,“如果你想研究严肃的遗传学,你需要去研究生院并获得博士学位。”
您选择在欧洲攻读研究生。为什么在那里?
我选择马德里自治大学是因为我想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并且因为我想与 安东尼奥·加西亚-贝利多,20世纪杰出的发育遗传学家之一。当我读他的论文时,他似乎以一种其他人没有的方式思考发展。
后来想想这个决定,事后看来,这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还有另一个原因。如果我在美国完成研究生工作(这是我被鼓励做的),那么读研究生会比现在更加困难。在美国,你会感受到种族分裂的持续冲击。
您在加西亚-贝利多 (García-Bellido) 指导下撰写的关于果蝇种系选择的博士论文, 对发育遗传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何如此轰动?
因为我为一些长期以来被假设但之前没有展示过的东西提供了直接的实验证据。也就是说,就像整个动物可以接受自然选择一样,适合的动物比不适合的动物生存得更好,发育中的动物体内的单个生殖细胞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生殖细胞之所以令人着迷,是因为它们是多细胞生物体中一种特殊的新奇事物。几乎所有主要成功的多细胞生命形式都用生殖细胞繁殖。它们是基因从一代传到另一代的方式。它们使细胞能够粘在一起,或形成像香蕉或人一样的大型多细胞聚集体。
介绍
所以你证明了果蝇体内的生殖细胞正在竞争。但以什么方式呢?他们的竞争的性质是什么?
由于组织中自发产生的突变,生物体中不同的生殖细胞可能具有略有不同的基因。这些突变会影响生殖细胞的生长和产生成功的卵子或精子的能力,这使它们在自然选择方面处于竞争状态。但事实证明,许多相同的基因也会影响身体其他部位的发育过程。因此,生殖细胞之间的这种选择过程会对所产生的后代一生的健康和健康产生重大影响。
你的论文对进化生物学有很强的影响,不是吗?
它做了。了解如何进化遗传程序来制造生殖细胞的微小子集非常重要。
我随后的职业生涯大部分都是为了了解单个细胞(受精卵)如何创造出由数百万个细胞组成的复杂的多细胞成体。我试图弄清楚生物体中不同类型的细胞最初是如何产生的。
我要问的问题之一是:他们怎么知道该怎么做?他们使用什么基因来做到这一点?既然地球上的第一个生命是单细胞的,那么多细胞基因和细胞类型最初是如何进化的呢?
当您尝试了解生殖细胞时,您的音乐兴趣发生了什么变化?
一路走来,我找到了同时从事科学和音乐的方法。在马德里工作期间以及后来在英国剑桥做博士后时,我仍然研究语音。此外,我还参加周末的试镜和表演。
当我攻读博士学位和博士后期间,我的声乐老师在瑞士。他在马德里还有其他学生,他大约每六周就会来西班牙和我们一起工作。有时,我会飞往巴塞尔上课。我会把他的课程录下来,然后再学习。
当然,有时这两种利益会发生冲突。完成博士学位后,我的声乐老师鼓励我全身心投入唱歌。 “你现在26岁了,”他说。 “是时候认真对待你的声音了。机不可失,勿失良机。”
我考虑了他的论点。但我对生物学非常感兴趣。归根结底,我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做到这两点。
幸运的是,作为一名研究生和博士后,我有非常资深的首席研究员,他们给了我很大的独立性。只要我按照预期的高水平完成工作,我就可以制定自己的时间表。
这可能意味着要在实验室多花几个晚上让果蝇成型,因为我无法在巡演时照顾它们。或者把苍蝇放在包里,这样我就不必停止实验。
介绍
你和动物学家一起做了你的博士后 迈克尔·阿卡姆 在剑桥。在生物化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对整个动物的研究有时看起来像是回到了另一个世纪。你为什么选择它?
因为我想将论文中的发现带到下一步。该论文研究了生殖细胞在一只动物中的行为。在剑桥,我询问所有动物的生殖细胞如何表现以及它们如何进化。为此,我在实验室研究了海胆、甲壳类动物和海葵。然后我阅读了历史文献,几乎所有关于数百个不同物种的生殖细胞的出版物。
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一直试图以以前的发现为基础,这有时意味着超出原始学科或扩展其定义。现在,在我的实验室,我们试图通过考虑基因以外的因素来理解发育的进化。
我们正在将生态和环境纳入我们的研究中。我们不只是孤立地研究果蝇,而是研究生活在果蝇体内的微生物以及果蝇赖以生存的植物。通过这项工作,我们希望了解发育过程如何在现实生活环境中演变。
您认为哈佛实验室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
首先,表明细胞间信号传导对于动物来说并不是一种不寻常的方式 产生胚胎生殖细胞 ——也就是说,将成为卵子和精子的细胞。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导教科书的观点是,在昆虫和大多数其他动物中,卵子中的“种质”在发育的早期就建立了独特的生殖细胞谱系。但我们发现,在蟋蟀中,周围组织的信号会诱导体细胞转变为生殖细胞。这也是小鼠和其他哺乳动物身上发生的情况,但它被认为是一种在进化中很少出现的新机制。
二、2020年发现失散多年的亲人 奥斯卡,一个因其在昆虫繁殖中的重要作用而闻名的基因,实际上是 来自细菌,不仅仅是来自早期的动物。该基因是通过细菌基因组序列与动物基因组序列融合而进化而来的。这表明先行者 奥斯卡 具有非常不同的功能,可能在神经系统的发育中,并且进一步研究它如何进化出新的目的可能会提供大量信息。
第三,伪造了具有百年历史的预测生物结构形状的“定律”。昆虫卵差异巨大,大小相差八个数量级,形状也截然不同。之前的假设是,某种适用于所有动物的普遍“法则”可以解释细胞形状和大小以及由细胞构成的结构的进化。就鸡蛋而言,之前有许多关于这些定律的假设,例如,鸡蛋的尺寸反映了每个物种的发育速度或成年体型的要求。
但我们构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数据集,包含 10,000 多个昆虫卵的测量数据,并发现: 真正能最好地预测鸡蛋的大小和形状的是它会产在哪里。卵产于地面或树叶下es 基本上是椭圆形的。产在水中的卵往往较小且呈球形。产在其他昆虫体内的寄生蜂卵也很小但不对称。
您是如何将工作从剑桥转移到哈佛的?
2003年,哈佛大学邀请我做一个研讨会。后来,人们说:“你知道进化发育生物学有一个助理教授职位空缺吗?你应该去申请。”
我在剑桥过得很开心。我刚刚获得了四年的研究经费。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不会得到这份工作,因为我很清楚哈佛正在寻找什么,但它看起来不像我。我很惊讶收到offer。
几年之内,你就获得了终身教职。事实上,您成为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生物科学领域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黑人女性。这感觉良好吗?还是像一种负担?
两个都。听着,这不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成为“第一”。作为全白人环境中唯一的黑人女性,本质上就是我职业生涯的故事。我选择的工作领域主要是白人。通常,每当我专业地做任何事情时,我都是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黑人女性。这不是对我的反映。这是场上的反映。
你在哈佛经历过任何偏见吗?
我没有经历过大量的故意封锁或有针对性的歧视。但事情常常会发生。我会出现在门口拿东西,然后被告知要使用服务入口。 “哦,我来这里参加[哈佛]公司的晚宴,”我解释道。 “哦,是的,服务入口就在后面。”
或者我是会议上的主讲人。我会去前台,听到:“您在等人吗?”
它是如此恒定。说我们应该像“这是鸭子背上的水”一样反应,意味着没有留下任何残留物。有大量疤痕组织堆积。我不能用我的大脑空间来容纳其中的每一个,因为我需要我的大脑空间来做其他事情。
介绍
众所周知,攻读 STEM 学科高级学位的美国黑人相对较少。他们占总人口的14%,但仅占科学与工程博士生的7%。根据您所目睹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差异?
原因之一是因为实验和理论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学徒或看门人模型之上的。一个人通过导师或顾问获得职业生涯。培训师选择他们认同的学员。如果看门人属于某个群体,他们就会使该群体永存。
您能否利用您的职位来支持对科学职业感兴趣的少数族裔学生?
我竭尽全力为他们服务。当少数族裔学生需要时,我会优先与他们交谈。对于少数群体的学生来说,提供积极的存在和愿意的倾听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我为所有学生露面。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我常常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位黑人教授。对他们来说了解我很重要。
关于你生活的另一部分——音乐。你的音乐对你的科学有帮助吗?
我不会这么说——尽管当我唱歌时,我的大脑和身体确实从科学中得到了休息。
反之亦然。这两种追求都要求极高,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吸引人。改变活动让我有机会休息、补充能量,并在我忙于其他事情时在潜意识中思考事情。当我回来时,潜意识的事情就会回到表面。
也许存在一些重叠之处,因为它们都是创造性的解决问题的企业。在艺术中,你有一些东西可以交流。您选择媒介。你尝试完善你的表达方式,然后你就去做。在科学中,你收集资源,回答问题并将其传达给世界。从这一点来说,它们有些相似。
12 月,您作为乐团的一部分在纽约林肯中心表演了亨德尔的作品 弥赛亚。您如何准备这样的表演?
老实说,我想象成功。当我们在后台等待入场时,我脑海中浮现出演出的结束和掌声。我想象着全场起立鼓掌,看到前排的人们脸上洋溢着喜悦的表情。我想象自己在表演时:感觉自由,感觉充满音乐,感觉我的身体是音乐交流的容器。
当你有机会时,你是否曾后悔没有搬到瑞士并全职追求音乐?
不。科学是一个让我获得了令人惊奇和令人兴奋的职业生涯的选择:我花了大部分时间试图了解多细胞生命和生殖细胞的起源,而这实际上是我的有偿工作!我想继续选择这个。超级有趣又好玩。
- :具有
- :是
- :不是
- :在哪里
- ][p
- $UP
- 000
- 10
- 2000
- 2014
- 2020
- 20日
- 26%
- a
- 对,能力--
- Able
- 关于
- 关于它
- AC
- 学者
- 接受
- ACCESS
- 事故
- 精准的
- 活动
- 通
- 成人
- 高级
- 影响
- 后
- 年龄
- 所有类型
- 几乎
- 沿
- 已经
- 还
- 时刻
- am
- 惊人
- 美国人
- 其中
- 量
- an
- 和
- 动物
- 动物
- 附件
- 另一个
- 回答
- 任何
- 什么
- 出现
- 应用的
- 使用
- 保健
- 论点
- 出现
- 围绕
- 艺术
- 艺术
- AS
- 问
- 财富
- 助理
- 假设
- 假设
- At
- 自主性
- 背部
- 后台
- 菌
- 坏
- 袋
- 香蕉
- 基于
- 巴塞尔
- 基本上
- BE
- 成为
- 因为
- 成为
- 很
- 背后
- 作为
- 最佳
- 更好
- 偏见
- 大
- 生物学
- 黑色
- 重磅炸弹
- 身体
- 波士顿
- 都
- 大脑
- 午休
- 带来
- 广播
- 建立
- 负担
- 但是
- by
- 被称为
- 剑桥
- CAN
- 加拿大
- 加拿大
- 寻找工作
- 人才招聘
- 携带
- 案件
- 细胞
- 细胞
- Center
- 世纪
- 一定
- 挑战
- 机会
- 更改
- 改变
- 儿童
- 选择
- 选择
- 选择
- 选择
- 明晰
- 类
- 清除
- 学院
- 结合
- 如何
- 通信
- 沟通
- 公司
- 竞争
- 竞争
- 竞争
- 完全
- 复杂
- 音乐会
- 研讨会 首页
- 砾岩
- 考虑
- 考虑
- 常数
- 构建
- 公司
- 可以
- 数
- 套餐
- 创建
- 创造
- 创意奖学金
- 好奇
- data
- 天
- 十二月
- 决定
- 决定
- 无疑
- 定义
- 喜悦
- 严格
- 设计
- 台
- 发达
- 发展
- 研发支持
- 发展的
- DID
- 不同
- 难
- 尺寸
- 晚餐
- 直接
- 纪律
- 学科
- 断开的
- 发现
- 不同
- 多元化
- 您所属的事业部
- do
- 不
- 占主导地位
- 完成
- 别
- 门
- 向下
- 驱动器
- 鼓
- ,我们将参加
- 每
- 此前
- 最早
- 早
- 地球
- 影响
- 蛋类
- 八
- 其他
- 鼓励
- 结束
- 从事
- 从事
- 工程师
- 更多
- 企业
- 完全
- 环境
- 环境中
- 时代
- 特别
- 必要
- 本质上
- 成熟
- 建立
- 欧洲
- 甚至
- 终于
- EVER
- 所有的
- 一切
- 证据
- 进化
- 发展
- 进化
- 例子
- 兴奋
- 令人兴奋的
- 存在
- 预期
- 有经验
- 实验
- 试验
- 实验
- 说明
- 解释
- 表示
- 表达
- 额外
- 非常
- 面孔
- 事实
- 秋季
- 家庭
- 家庭
- 著名
- 迷人
- 反馈
- 感觉
- 感觉
- 少数
- 部分
- 数字
- 满
- 找到最适合您的地方
- 发现
- 姓氏:
- 第一次
- 适合
- 运动健身
- 重点
- 针对
- 申请
- 幸运
- 发现
- 公司成立
- 四
- Free
- 友好
- 止
- 前
- ,
- 开玩笑
- 功能
- 资金
- 进一步
- 聚变
- 获得
- 收益
- 游戏
- 看门人
- 收集
- 给
- 代
- 遗传
- 基因
- 得到
- 越来越
- 给
- 给
- Go
- 去
- 非常好
- 得到了
- 毕业
- 大
- 陆运
- 团队
- 增长
- 长大的
- 制导
- 民政事务总署
- 手
- 发生
- 发生
- 快乐
- 哈佛
- 哈佛大学
- 有
- he
- 健康管理
- 听
- 保持
- 这里
- 相关信息
- 高
- 高度
- 他
- 事后
- 他的
- 历史性
- 举行
- 诚实的
- 抱有希望
- 创新中心
- HTML
- HTTPS
- 巨大
- 谦逊
- 数百
- i
- 生病
- 主意
- 鉴定
- 身份
- if
- 想像
- 想象
- 影响力故事
- 启示
- 重要
- in
- 包含
- 结合
- 令人难以置信
- 独立
- 个人
- 影响
- 信息
- 信息
- 内
- 例
- 代替
- 研究所
- 仪器
- 文书
- 兴趣
- 有兴趣
- 有趣
- 利益
- 专属采访
- 面试
- 成
- 调查
- 请帖
- 邀请
- 隔离
- IT
- 它的
- 工作
- 只是
- 保持
- 主题演讲
- 主讲人
- 类
- 知道
- 已知
- 实验室
- 实验室
- 奠定了
- 地标
- 大
- 晚了
- 后来
- 法律
- 学习用品
- 最少
- 导致
- 左
- 减
- 教训
- 让
- Level
- 自学资料库
- 生活
- 喜欢
- 林肯
- 血统
- 线
- 清单
- 听
- 文学
- 生活
- 生活
- 活的
- 逻辑
- 长
- 看
- 看起来像
- 寻找
- LOOKS
- 占地
- 制成
- 杂志
- 主要
- 多数
- 专业
- 使
- 男子
- 许多
- 掌握
- 数学
- me
- 意味着
- 手段
- 测量
- 机制
- 机制
- 医生
- 中等
- 导师
- 可能
- 百万
- 介意
- 头脑
- 线粒体
- 模型
- 美好瞬间
- 更多
- 此外
- 最先进的
- 母亲
- 移动
- 多
- 音乐
- 音乐
- 音乐家
- my
- 我自己
- 亦即
- 自然
- 自然
- 需求
- 打印车票
- 决不要
- 全新
- 纽约
- 下页
- 没有
- 注意..
- 小说
- 新奇
- 现在
- 可能性
- of
- 折扣
- 提供
- 办公
- 经常
- 老年人
- on
- 一
- 仅由
- 猛攻
- 开放
- or
- 订单
- 原版的
- 起源
- 其他名称
- 其它
- 我们的
- 输出
- 学校以外
- 超过
- 交叠
- 己
- 支付
- 文件
- 父母
- 部分
- 部分
- 通过
- 通过
- 员工
- 完美
- 性能
- 执行
- 执行
- 施行
- 也许
- 永存
- 人
- 亲自
- 挑
- 采摘的
- 件
- 地方
- 计划
- Plants
- 柏拉图
- 柏拉图数据智能
- 柏拉图数据
- 播放
- 人口
- 位置
- 积极
- 或者
- 在练习上
- 都曾预测
- 主要
- 杰出的
- Prepare
- 存在
- 呈现
- 漂亮
- 以前
- 先前
- 校长
- 优先
- 问题解决
- 过程
- 过程
- 生产
- 生成
- 所以专业
- 专业
- 教授
- 曲目
- 蛋白质
- 证明
- 提供
- 提供
- 提供
- 出版
- 目的
- 追求
- 认沽期权
- 困扰
- 修饰
- 量子杂志
- 题
- 有疑问吗?
- 很快
- 凸
- 随机
- 很少
- 率
- 应对
- 阅读
- 现实
- 实现
- 真
- 原因
- 接收
- 最近
- 最近
- 承认
- 记录
- 反映
- 反射
- 遗憾
- 经常
- 相对
- 亲属
- 卓越
- 再生
- 代表
- 复制
- 必须
- 岗位要求
- 研究
- 研究
- 资源
- 尊重
- 响应
- REST的
- 回报
- 右
- 角色
- 行
- s
- 说
- 同
- 对工资盗窃
- 说
- 始你
- 学校
- 科学
- 科学
- 科学家
- SEA
- 看到
- 看到
- 寻求
- 似乎
- 似乎
- 选择
- 研讨会
- 前辈
- 分开
- 严重
- 服务
- 集
- 形状
- 形状
- 她
- 应该
- 显示
- 显示
- 显示
- 如图
- 作品
- 信号
- 类似
- 自
- 单
- 坐在
- 情况
- SIX
- 尺寸
- 尺寸
- 略有不同
- 小
- 小
- So
- 社会
- 一些
- 有人
- 东西
- 有时
- 有些
- 声音
- 太空
- 西班牙
- 西班牙语
- 喇叭
- 特别
- 特别是
- 花
- 花费
- 地位
- 开始
- 州
- 干
- 步
- 仍
- Stop 停止
- 故事
- 强烈
- 结构
- 学生
- 学生
- 研究
- 研究
- 学习
- 留学
- 主题
- 随后
- 成功
- 成功
- 这样
- 提示
- 超级
- SUPPORT
- 支持
- 磁化面
- 感到惊讶
- 周围
- 瑞士
- 系统
- 采取
- 拍摄
- 天才
- 说
- 针对
- 教
- 教诲
- 团队
- 易于
- 比
- 这
- 世界
- 其
- 他们
- 然后
- 理论
- 那里。
- 博曼
- 他们
- 事
- 事
- 认为
- 思维
- Free Introduction
- 那些
- 虽然?
- 思想
- 三
- 通过
- 始终
- 次
- 至
- 今晚
- 一起
- 告诉
- 也有
- 了
- 工具
- 多伦多
- 完全
- 教程
- 镇
- 熟练
- 巨大
- 异常
- 尝试
- 三位一体
- true
- 尝试
- 试图
- 转
- 原来
- 二
- 类型
- 英国
- 我们
- 下
- 理解
- 理解
- 了解
- 联合的
- 美国
- 普遍
- 大学
- 空前的
- 敦促
- us
- 使用
- 有用
- 折扣值
- 变化
- 反之亦然
- 非常
- 船只
- 副
- 音色
- 等候
- 想
- 通缉
- 希望
- 希望
- 是
- 水
- 方法..
- 方法
- we
- 网页
- 周
- 欢迎进入
- 井
- 为
- 什么是
- ,尤其是
- 每当
- 这
- 而
- 白色
- WHO
- 全
- 为什么
- 广泛
- 广泛
- 将
- 愿意
- 赢
- 风
- WISE
- 中
- 目击
- 女子
- 韩元
- 工作
- 工作
- 加工
- 世界
- 价值
- 将
- 年
- 年
- 含
- 但
- 纽约
- 完全
- 年轻
- 您一站式解决方案
- 你的
- 和风网
- 动物园
- 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