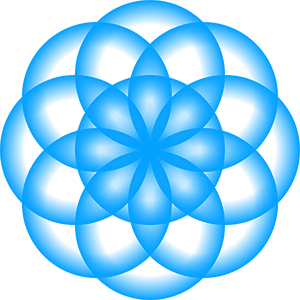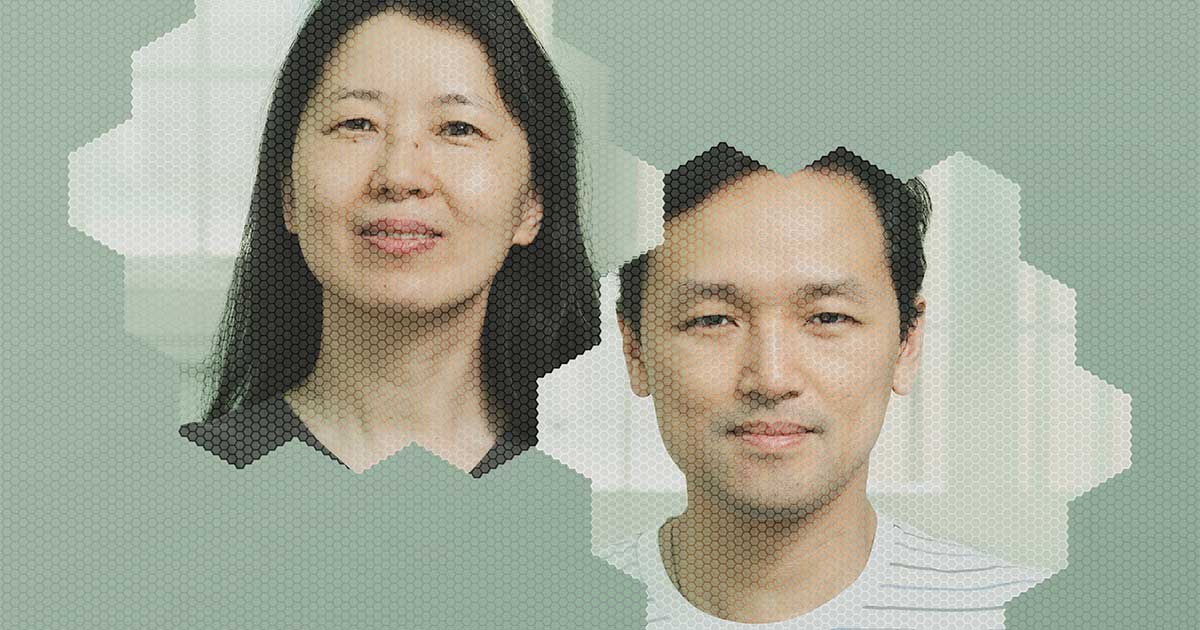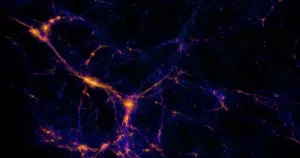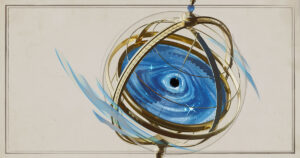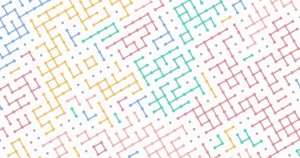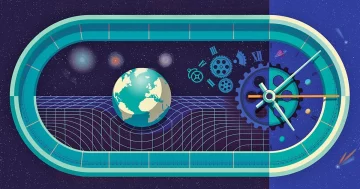即使对于训练有素的人来说,辉钼矿看起来也几乎与石墨相同——一种有光泽的银色晶体。它的作用也类似,以一种可以很好地填充铅笔的方式脱落薄片。但对于电子来说,两个原子网格形成了不同的世界。 244 年前,这一殊荣首次被记录在科学记录中。瑞典化学家卡尔·舍勒因发现氧气而闻名,他将每种矿物质浸入各种酸中,观察滚滚而出的可怕气体云。 Scheele 最终为这种方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43 岁死于疑似重金属中毒,他得出的结论是辉钼矿是一种新物质。他在 1778 年写给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一封信中对此进行了描述,他写道:“我在这里指的不是人们可以从药剂师那里获得的众所周知的石墨。这种过渡金属似乎是未知的。”
由于辉钼矿易于剥落成粉状碎片,因此成为 20 世纪流行的润滑剂。它帮助滑雪板在雪地里滑得更远,并使子弹从越南的步枪枪管中顺利射出。
如今,同样的脆弱性正在推动一场物理学革命。
突破始于石墨和透明胶带。研究人员在 2004 年偶然发现,他们可以使用胶带剥离只有一个原子厚度的石墨片。这些晶体片都是由碳原子组成的平面阵列,具有与它们所来源的三维晶体完全不同的惊人特性。石墨烯(正如它的发现者所称的那样)是一种全新的物质类别——一种二维材料。它的发现改变了凝聚态物理学,这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旨在理解物质的多种形式和行为。 近一半 的物理学家是凝聚态物理学家;这个子领域为我们带来了计算机芯片、激光器、LED 灯泡、MRI 机器、太阳能电池板和各种现代技术奇迹。石墨烯被发现后,数千名凝聚态物理学家开始研究这种新材料,希望它能够巩固未来的技术。
石墨烯的发现者于 2010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同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年轻物理学家, 界山 和 麦建辉,看到有迹象表明辉钼矿薄片可能比石墨烯更神奇。这种鲜为人知的矿物具有难以研究的特性——对于许多实验室来说太难了——但它却吸引了 Shan 和 Mak。这对顽强的二人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来研究二维辉钼矿(或二硫化钼,实验室培育的晶体被称为)和一系列密切相关的二维晶体。
现在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单和麦现已结婚并在康奈尔大学管理着一个联合研究小组,他们已经证明,二硫化钼及其亲属的二维晶体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奇异量子现象。 “这是一个疯狂的游乐场,”说 詹姆斯·霍恩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为康奈尔大学实验室提供高质量的晶体。 “你可以在一种材料系统中完成所有现代凝聚态物理学。”
Shan 和 Mak 的团队捕获了电子在这些扁平晶体中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现。他们诱使粒子融合成量子流体并冻结成各种冰状结构。他们学会了组装巨大的人造原子网格,这些网格现在被用作物质基础理论的试验台。自 2018 年在康奈尔大学开设实验室以来,电子驯服大师已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八篇论文。 自然,科学领域最负盛名的期刊,以及大量其他论文。理论家表示,这对夫妇正在扩大对电子群能力的理解。
他们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令人印象深刻”,说 菲利普·金哈佛大学著名凝聚态物理学家。 “我想说,这是耸人听闻的。”
二维材料的兴起
材料的属性通常反映其电子的行为。例如,在金属等导体中,电子可以轻松地在原子之间航行并携带电力。在木材和玻璃等绝缘体中,电子保持原样。像硅这样的半导体介于两者之间:它们的电子可以被迫随着能量的涌入而移动,这使得它们成为开关电流的理想选择——这是晶体管的工作。在过去的 50 年里,除了这三种基本的电子行为之外,凝聚态物理学家还发现了轻质带电粒子以许多更奇特的方式表现。
更戏剧性的惊喜之一发生在 1986 年,当时两位 IBM 研究人员 Georg Bednorz 和 Alex Müller, 检测 电子流穿过氧化铜(“铜酸盐”)晶体,没有任何阻力。这种超导性——电力以完美效率流动的能力——以前就已经出现过,但只是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材料冷却到绝对零的几度以内。这一次,Bednorz 和 Müller 观察到了这种现象的一种神秘形式,这种现象在破纪录的 35 开尔文(即高于绝对零度 35 度)的温度下持续存在。科学家们很快发现了其他超导温度超过 100 开尔文的铜酸盐。一个梦想诞生了,也许仍然是当今凝聚态物理学的首要目标:找到或设计一种可以在我们炎热的、大约 300 开尔文的世界中超导电力的物质,从而实现无损电力线、悬浮车辆和其他超高效设备,将大大减少人类的能源需求。
超导性的关键是诱导通常相互排斥的电子配对并形成称为玻色子的实体。然后玻色子可以集体融合成无摩擦的量子流体。产生玻色子的吸引力,例如原子振动,通常只能在低温或低温下才能克服电子的排斥力。 高压。但对这些极端条件的需求阻碍了超导技术进入日常设备。铜酸盐的发现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即正确的原子晶格可以将电子牢固地“粘合”在一起,即使在室温下它们也能保持粘在一起。
Bednorz 和 Müller 的发现已经过去了 40 年,理论家们仍然不能完全确定铜酸盐中的胶水是如何工作的,更不用说如何调整材料来增强它的强度了。因此,凝聚态物理领域的许多研究都是对晶体的反复试验,寻找可以使电子保持配对或以其他奇妙方式引导电子的晶体。 “凝聚态物质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它允许偶然发现,”金说。这就是 2004 年二维材料的发现。
安德烈·海姆 和 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与石墨合作, 发现 材料片状的结果令人震惊。石墨晶体含有排列成松散结合的六边形片的碳原子。理论家早就预测,如果没有堆栈的稳定影响,热引起的振动会破坏单层片材。但海姆和诺沃肖洛夫发现,他们只需要透明胶带和坚持就可以剥离稳定的原子级薄片。石墨烯是第一种真正平坦的材料——电子可以在其上滑动但不能上下滑动的平面。
哥伦比亚物理学家霍恩发现世界上最薄的材料不知何故 也是最强的。对于理论家认为根本无法粘合在一起的材料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物理学家对石墨烯最感兴趣的是碳平地如何转变电子:没有什么可以减慢它们的速度。电子经常会被它们移动的原子晶格绊倒,其作用比教科书上的质量重(绝缘体中不动的电子的作用就好像它们具有无限的质量一样)。然而,石墨烯的扁平晶格可以让电子以每秒一百万米的速度呼啸而过——只比光速慢几百倍。在这种恒定的、惊人的速度下,电子飞行时就好像它们根本没有质量一样,从而使石墨烯具有极端(尽管不是超级)的导电性。
围绕着这种奇妙的材料,出现了整个领域。研究人员也开始进行更广泛的思考。其他物质的二维薄片能否拥有自己的超能力?霍恩就是其中之一。 2 年,他测量了石墨的分身二硫化钼的一些机械性能,然后将晶体交给托尼·海因茨哥伦比亚实验室的两位光学专家。这是一个偶然的举动,却改变了所有相关人员的职业生涯。
二硫化钼样品落到了职业生涯早期的客座教授单杰和研究生麦健辉手中。这对年轻的二人组正在研究石墨烯如何与光相互作用,但他们已经开始幻想其他材料。石墨烯的快速电子使其成为一种神奇的导体,但他们想要的是一种二维半导体——一种可以打开和关闭电子流的材料,因此可以用作晶体管。
已知二硫化钼是一种半导体。 Shan 和 Mak 很快发现,就像石墨一样,它在二维中获得了额外的能力。当他们用激光照射“二硫化钼”(他们亲切地称呼它)的 2D 晶体时,晶体保持黑暗。但是,当 Shan 和 Mak 用透明胶带撕下层,用激光照射它们,并在显微镜下检查它们时,他们看到二维薄片闪闪发光。
其他小组的研究后来证实,制作精良的密切相关材料薄片会反射撞击它们的最后一个光子。 “这有点令人难以置信,”最近,当我在康奈尔大学的共用办公室见到他和单时,他说道。 “你只有一片原子,它可以像一面完美的镜子一样反射 100% 的光。”他们意识到这一特性可能会带来壮观的光学设备。
独立地, 王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家也做出了同样的发现。一种高反射率的二维材料和半导体引起了社区的关注。 以上皆是 团体 2010 年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此后,这些论文已被引用超过 16,000 次。 “每个使用激光器的人都开始对二维材料非常感兴趣,”霍恩说。
通过将二硫化钼确定为第二种二维神奇材料,两个小组登陆了整个二维材料大陆。二硫化钼属于过渡金属二硫族化物 (TMD) 物质家族,其中元素周期表金属中间区域的原子(例如钼)与称为硫族化物的化合物对(例如硫)连接。二硫化钼是唯一天然存在的 TMD,但也有 还有几十个 研究人员可以在实验室中制造二硫化钨、二碲化钼等。大多数形成弱结合片材,使它们容易受到胶带商业面的影响。
然而,最初的兴奋浪潮很快就消退了,因为研究人员努力让 TMD 不仅仅发挥作用。例如,王的团队在发现无法轻松地将金属电极连接到二硫化钼上后,转而使用石墨烯。 “多年来,这一直是我们团队的绊脚石,”他说。 “即使现在我们也不太擅长建立联系。” TMD 相对于石墨烯的主要优点似乎也是它们最大的弱点:为了研究材料的电子特性,研究人员必须经常将电子推入其中并测量产生的电流的电阻。但由于半导体是不良导体,因此电子很难进出。
麦和珊最初感到矛盾。 “我们真的不清楚是否应该继续研究石墨烯或开始研究这种新材料,”麦说。 “但自从我们发现它具有这种良好的特性后,我们继续做了更多的实验。”
在工作过程中,两位研究人员对二硫化钼以及彼此越来越着迷。最初,他们的联系是专业的,主要限于以研究为重点的电子邮件。 “Fai 经常问,‘那件设备在哪里?你把它放在哪里了?’”单说。但最终他们的关系在长时间的培育和实验成功的催化下变得浪漫。 “我们只是经常见面,实际上是在同一个实验室从事同一个项目,”麦说。 “这个项目进展顺利也让我们很高兴。”
所有物理时刻
需要两位具有铁一般纪律的虔诚物理学家合作,才能让麻烦的 TMD 屈服。
学者们总是很容易来到掸邦。她在 1970 世纪 XNUMX 年代的沿海省份浙江长大,是一名明星学生,在数学、科学和语言方面表现出色,并在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得了令人垂涎的学位。在那里,她获得了参加中苏文化交流项目的资格,并抓住了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俄语和物理学的机会。 “当你十几岁的时候,你渴望探索世界,”她说。 “我没有犹豫。”
立刻,她看到了比她预想的更多的世界。由于签证问题,她推迟了几个月抵达俄罗斯,并失去了语言项目的席位。当局为她找到了另一条路线,抵达莫斯科后不久,她就登上了火车,向东行驶了 5,000 公里。三天后,她抵达了西伯利亚中部的伊尔库茨克市,时值初冬。 “我得到的建议是,‘永远、永远不要不戴手套触摸任何东西’”,以免她被卡住,她说。
单戴上手套,在一个学期内学会了俄语,并开始欣赏冬日风景的荒凉之美。当课程结束、雪融化后,她回到首都开始攻读物理学学位,并于 1990 年春天抵达莫斯科,当时正值苏联解体。
那是混乱的岁月。当共产党试图重新控制政府时,单看到坦克在大学附近的街道上行驶。还有一次,期末考试刚结束,就发生了打架事件。 “我们听到枪声,我们被告知要关掉宿舍里的灯,”她说。从食物到卫生纸,所有东西都通过优惠券系统配给。尽管如此,单女士还是受到了教授们坚忍不拔的精神的鼓舞,尽管经历了动荡,他们仍然继续他们的研究。 “条件虽然艰苦,但很多科学家都有这样的态度。不管发生了什么,他们真的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她说。
随着世界秩序的崩溃,单珊脱颖而出,发表了一篇理论光学论文,引起了哥伦比亚大学海因茨的注意。他鼓励她申请,然后她搬到了纽约,在那里她偶尔帮助其他国际学生在国外站稳脚跟。例如,她招募王到亨氏实验室工作,并分享实验技巧。 “她教我如何保持耐心,”他说,“如何不因激光而感到沮丧。”
大多数研究人员在获得博士学位后都会从事博士后职位,但单女士于 2001 年直接加入凯斯西储大学担任副教授。几年后,在休假期间,她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亨氏实验室。这一次,她的时机是偶然的。她开始与 Heinz 团队中一位迷人、目光明亮的研究生麦健辉 (Kin Fai Mak) 合作。
麦沿着一条不同的、不那么喧闹的道路来到了纽约市。他在香港长大,在学校里很挣扎,因为除了物理之外,他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这是我唯一喜欢并且实际上擅长的事情,所以我选择了物理,”他说。
他在香港大学的本科研究表现出色,亨氏招募他加入哥伦比亚大学蓬勃发展的凝聚态物理项目。在那里,他全身心投入研究,除了偶尔参加校内足球比赛外,几乎所有醒着的时间都在实验室里度过。研究生安德里亚·杨(Andrea Young,现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助理教授)与麦在西 113 街合租一套公寓。 “如果我能在凌晨 2 点和他一起煮一些意大利面并谈论物理,我就很幸运了。这一直都是物理学,”杨说。
但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与杨一起游览哥伦比亚的亚马逊雨林后不久,麦就病倒了。他的医生不确定如何看待他令人费解的测试结果,他的病情变得更加严重。一次幸运的巧合救了他的命。杨向他的父亲(一名医学研究员)描述了这种情况,他立即意识到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迹象——一种不寻常的血液疾病,恰好是他自己研究的主题。 “首先,这种疾病实际上很少见,”麦说。 “更罕见的是,患上你室友父亲擅长治疗的疾病。”
杨的父亲帮助麦参加了实验性治疗。他研究生最后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度过,并多次濒临死亡。在整个磨难过程中,麦对物理学的热情驱使他继续工作。 “他正在写 泌乳素 他在病床上写下的信,”杨在谈到这本日记时说道 “物理评论快报”。 “尽管如此,他仍然是有史以来最有成效的学生之一,”海因茨说。 “这真是一个奇迹。”
进一步的治疗最终帮助麦完全康复。杨本人就是一位著名的实验学家,他后来对自己的干预行为打趣道:“在朋友中,我称这是我对物理学的最大贡献。”
进入二维荒野
2012 年,Mak 前往康奈尔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此时 Shan 已经回到 Case Western。他们利用石墨烯和其他材料开展了单独的项目,但他们也继续共同揭开 TMD 的更多秘密。
在康奈尔大学,麦学习了电子传输测量的艺术——这是除光学之外预测电子运动的另一种主要方法。这种专业知识使他和单在研究人员通常专注于其中一种类型的领域中成为双重威胁。 “每当我见到辉和杰时,我都会抱怨,‘你们做运输是不公平的,’”金说。 “我应该做些什么?”
两人对 TMD 了解得越多,就越感兴趣。研究人员通常关注电子的两个属性之一:它们的电荷和自旋(或内在角动量)。控制电荷流动是现代电子学的基础。翻转电子的自旋可能会导致“自旋电子学”设备将更多信息装入更小的空间。 2014年, 麦帮助发现 二维二硫化钼中的电子可以获得特殊的第三个属性:这些电子必须以特定量的动量移动,这是一种被称为“谷”的可控属性,研究人员推测它可能会催生“谷电子学”技术的第三个领域。
同年,Mak 和 Shan 发现了 TMD 的另一个显着特征。电子并不是唯一穿过晶体的实体。物理学家还追踪“空穴”,即电子跳跃到其他地方时产生的空位。这些孔可以像真正的带正电粒子一样在材料中漫游。在电子堵塞空穴之前,正空穴吸引负电子形成短暂的伙伴关系,称为激子。单和麦 测量吸引力 研究人员对 2D 二硒化钨中的电子和空穴之间的电子和空穴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强度比典型 3D 半导体强数百倍。这一发现暗示TMD中的激子可能特别强大,而且一般来说电子更有可能做各种奇怪的事情。
这对夫妇一起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获得了职位,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实验室。最终,他们确信 TMD 值得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并将这些材料作为新团队的重点。他们也结婚了。
与此同时,哥伦比亚大学的霍恩团队发现,当他们将石墨烯放置在高质量绝缘体氮化硼上时,石墨烯的性能变得更加极端。这是二维材料最新颖的方面之一的早期例子:它们的可堆叠性。
将一种二维材料放在另一种材料之上,各层之间的距离只有几分之一纳米——从电子的角度来看,根本没有距离。结果,堆叠的片材有效地合并成一种物质。 “这不仅仅是两种材料的结合,”王说。 “你真的创造了一种新材料。”
虽然石墨烯仅由碳原子组成,但 TMD 晶格的多样化系列为堆叠游戏带来了数十种额外元素。每个TMD都有自己固有的能力。有些是磁性的;有些是磁性的。其他人超导。研究人员期待将它们与时尚材料混合搭配,发挥它们的综合力量。
但是,当霍恩的团队将二硫化钼放置在绝缘体上时,与他们在石墨烯中看到的相比,堆叠的性能表现出平淡无奇的进步。最终他们意识到他们没有检查TMD晶体的质量。当他们让一些同事将二硫化钼放在能够分辨单个原子的显微镜下时,他们惊呆了。一些原子位于错误的位置,而另一些原子则完全消失了。多达百分之一的晶格位置存在问题,阻碍了晶格引导电子的能力。相比之下,石墨烯是完美的形象,大约每百万个原子就有一个缺陷。 “我们终于意识到我们买的东西完全是垃圾,”霍恩说。
2016年左右,他决定进入研究级TMD的种植业务。他招募了一名博士后, 丹尼尔·罗德斯,拥有通过在极高温度下熔化原材料粉末,然后以极快的速度冷却来生长晶体的经验。 “这就像用水中的糖来种植冰糖一样,”霍恩解释道。新过程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而商业方法只需几天。但它生产的 TMD 晶体比化学品目录中出售的晶体好数百到数千倍。
在 Shan 和 Mak 能够利用 Hone 日益纯净的晶体之前,他们面临着一项乏味的任务,即弄清楚如何处理不喜欢接受电子的微观薄片。为了泵入电子(Mak 作为博士后学到的传输技术的基础),这对夫妇痴迷于无数的细节:电极使用哪种类型的金属,放置电极距离 TMD 多远,甚至使用哪种化学物质用于清洁触点。尝试无数种设置电极的方法既缓慢又费力——“一个一点点改进这个或改进那个的耗时过程,”麦说。
他们还花了数年时间研究如何举起和堆叠这些微小的薄片,这些薄片的宽度只有百万分之一米。凭借这种能力,加上 Hone 的晶体和改进的电接触,一切都在 2018 年实现了。这对夫妇搬到了纽约州伊萨卡,在康奈尔大学担任新职位,他们的实验室涌现出一系列开创性成果。
康奈尔大学的突破
“今天,由于某种原因,一切都很难恢复,”Mak 和 Shan 小组的研究生 Zenchao Xia 说道,此时氮化硼薄片的黑色轮廓有可能脱落并落回下面的硅表面。马达加斯加形状的薄片无力地粘在一块类似沙特阿拉伯的石墨上,就像纸粘在最近摩擦的气球破裂的表面上一样。石墨又粘在玻璃载玻片上粘稠的塑料露珠上。夏使用计算机界面来控制夹住幻灯片的电动支架。就像街机玩家用操纵杆操纵抓娃娃机一样,她小心翼翼地以每点击一次鼠标,百万分之一米五分之一的速度将一堆东西举到空中,专心地盯着电脑显示器,看看她是否有成功捕获氮化硼薄片。
她有。再点击几下,两层堆叠就自由了,夏迅速但故意地将薄片沉积到嵌入了蔓延的金属电极的第三种材料上。又按了几下,她加热了表面,在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打喷嚏把这个微型装置拿走之前,就融化了载玻片的塑料粘合剂。
“我总是做这样的噩梦,它就这样消失了,”她说。
从开始到完成,夏花了一个多小时才组装了一个简单设备的下半部分——相当于一个开放式的 PB&J。她向我展示了她最近组装的另一堆材料,并快速说出了一些成分,其中包括 TMD 二硒化钨和二碲化钼。她在去年制作并研究了数十个微型三明治,其中一个是达格伍德装置,它有 10 层之多,需要几个小时才能组装完成。
这种二维材料的堆叠也在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实验室中完成,代表了凝聚态物理学家长期以来的梦想的实现。研究人员不再局限于在地下发现的材料或在实验室中缓慢生长的材料。现在,他们可以玩乐高积木的原子等效物,将板材拼凑在一起,构建具有所需特性的定制结构。在组装 TMD 结构方面,很少有人能像康奈尔大学研究小组那样走得更远。
Mak 和 Shan 在康奈尔大学的第一个重大发现涉及激子,即他们早在 2014 年在 TMD 中看到的强束缚电子空穴对。激子引起了物理学家的兴趣,因为这些“准粒子”可能会提供一种迂回的方式来实现凝聚态物理的长期目标:室温超导。
激子遵循与电子-电子对相同的时髦规则。这些电子空穴对也变成玻色子,这让它们“凝聚”成一种共享的量子态,称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这种连贯的准粒子群可以表现出量子特性,例如超流动性,即无阻力流动的能力。 (当超流体携带电流时,它就会超导。)
但与排斥性电子不同,电子和空穴喜欢耦合。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会使他们的胶水更坚固。基于激子的超导性的挑战在于防止电子填充空穴,并使电中性对在电流中流动——所有这些都在尽可能温暖的房间内进行。到目前为止,Mak 和 Shan 已经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并制定了解决第二个问题的计划。
通过用强大的激光将原子云冷却到绝对零以上的头发丝,可以将原子云诱导形成凝聚物。但理论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怀疑激子凝聚可以在更高的温度下形成。康奈尔大学团队通过可堆叠 TMD 将这一想法变为现实。他们使用两层三明治,将额外的电子放在顶层,并从底部移走电子,留下空穴。电子和空穴配对,产生寿命很长的激子,因为电子很难跳到相反的层来中和它们的伙伴。 2019年XNUMX月,集团 报告的迹象 温度为 100 开尔文的激子凝聚体。在这种设置中,激子持续了数十纳秒,这是此类准粒子的寿命。 2021年秋季,该小组描述了一种改进的装置,其中激子似乎持续了几毫秒,麦称之为“几乎永远”。
目前团队正在追求 一个计划 理论家于 2008 年提出,用于产生激子电流。 艾伦·麦克唐纳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一位著名凝聚态理论家和他的研究生 Jung-Jung Su 提出,通过施加一个鼓励电子和空穴沿同一方向移动的电场来使中性激子流动。为了在实验室中实现这一目标,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小组必须再次应对他们的长期敌人——电接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将多组电极连接到 TMD 层,其中一些用于制造激子,另一些用于移动激子。
Shan 和 Mak 相信他们很快就能让激子以高达 100 开尔文的速度流动。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寒冷的房间(-173 摄氏度或-280 华氏度),但与大多数玻色子凝聚体所需的纳开尔文条件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成就,”麦狡猾地微笑着说,“让气温升高十亿倍。”
神奇的莫尔条纹材料
2018年,当康奈尔实验室加大TMD实验力度时,石墨烯的另一个惊喜引发了第二次二维材料革命。 巴勃罗·贾里洛·埃雷罗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和另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宣布,将一层石墨烯相对于下面的一层扭转,创造了一种神奇的新型二维材料。秘诀在于放下上层,使其六边形落地时稍微“扭曲”,这样它们就相对于下面的六边形精确旋转了 2 度。这种角度错位会导致原子之间的偏移,当您在材料上移动时,原子会增大和缩小,从而产生大型“超级晶胞”的重复图案,称为莫尔超晶格。麦克唐纳和一位同事 2011年计算 在 1.1 度的“魔角”下,超晶格独特的晶体结构将迫使石墨烯的电子减慢速度并感知相邻电子的排斥力。
当电子彼此意识到时,就会发生奇怪的事情。在普通绝缘体、导体和半导体中,电子被认为只与原子晶格相互作用。他们跑得太快而无法注意到对方。但速度慢得像爬行一样,电子可以相互碰撞并共同呈现出各种奇异的量子态。 Jarillo-Herrero 的实验表明,对于 知之甚少 由于这种原因,扭曲的魔角石墨烯中的电子间通信产生了 特别强的超导形式.
石墨烯莫尔超晶格还向研究人员介绍了一种控制电子的全新方法。在超晶格中,电子不再关注单个原子,而是将超级晶胞本身视为巨大的原子。这使得超级晶胞中充满足够的电子以形成集体量子态变得很容易。 Jarillo-Herrero 的团队利用电场来增加或减少每个超级电池的平均电子数,从而使他们的扭曲双层石墨烯装置充当超导体,充当超导体。 绝缘体,或显示 其他的木筏, 陌生电子行为.
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纷纷涌入“双旋电子学”这一新兴领域。但许多人发现扭转是很困难的。原子没有理由整齐地落入“神奇”的 1.1 度错位中,因此薄片会以完全改变其特性的方式起皱。康奈尔大学研究生夏说,她在其他大学有一群朋友正在研究扭曲的设备。创建一个可用的设备通常需要他们进行数十次尝试。即便如此,每个设备的行为都不同,因此特定的实验几乎不可能重复。
TMD 提供了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来创建莫尔超晶格。由于不同的 TMD 具有不同尺寸的六边形晶格,因此将稍大的六边形晶格堆叠在较小的晶格上会产生莫尔图案,就像角度未对准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各层之间没有旋转,因此堆叠更有可能卡入到位并保持静止。当 Xia 着手创建 TMD 摩尔纹设备时,她说,她通常五分之四会成功。
TMD 莫尔材料是探索电子相互作用的理想场所。由于这些材料是半导体,因此它们的电子在穿过材料时会变得很重,这与石墨烯中的狂热电子不同。巨大的莫尔晶胞进一步减慢了它们的速度:虽然电子通常通过“隧道”(一种类似于隐形传态的量子力学行为)在原子之间移动,但在莫尔晶格中很少发生隧道效应,因为超级晶胞的距离比其内部原子的距离大约远 100 倍。距离有助于电子稳定下来,并让它们有机会认识邻居。
Shan 和 Mak 的友好竞争对手 Wang Feng 是最早认识到 TMD 莫尔超晶格潜力的人之一。粗略计算表明,这些材料应该会产生电子最简单的组织方式之一——一种被称为维格纳晶体的状态,其中相互排斥将昏昏欲睡的电子锁定到位。王团队看到 这种状态的迹象 2020年并发表 第一张图片 电子以一臂的距离彼此保持 自然 2021年。那时,王的TMD莫尔条纹活动的消息已经在紧密的二维物理界传开,康奈尔大学的TMD工厂正在生产自己的TMD莫尔条纹装置。 Shan 和 Mak 还于 2 年报告了 TMD 超晶格中维格纳晶体的证据,并在几个月内发现他们设备中的电子几乎可以在 两打不同的维格纳水晶图案.
与此同时,康奈尔团队也正在将TMD摩尔纹材料制作成电动工具。麦克唐纳和合作者 曾预言 2018 年,这些设备拥有正确的技术特征组合,使它们完美地代表了凝聚态物理中最重要的玩具模型之一。哈伯德模型,顾名思义,是一个用于理解各种电子行为的理论系统。 独立提出 该模型由 Martin Gutzwiller、Junjiro Kanamori 和 John Hubbard 于 1963 年提出,是物理学家将几乎无穷无尽的晶格种类剥离到最基本特征的最佳尝试。想象一下含有电子的原子网格。哈伯德模型假设每个电子感受到两种竞争力量:它想要通过隧道效应移动到邻近的原子,但它也受到邻居原子的排斥,这使得它想要留在原处。根据哪种欲望最强烈,会出现不同的行为。哈伯德模型的唯一问题是,除了最简单的情况(一维原子串)之外,它在数学上是无法解决的。
MacDonald 及其同事表示,TMD 莫尔材料可以充当哈伯德模型的“模拟器”,有可能解决该领域的一些最深奥的谜团,例如将电子粘合到铜酸盐中的超导对中的胶水的性质。研究人员可以将电子放入 TMD 三明治中,看看它们会发生什么,而不是苦苦挣扎于一个不可能的方程。 “我们可以写下这个模型,但很难回答很多重要的问题,”麦克唐纳说。 “现在我们只需做一个实验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确实具有开创性。”
为了构建他们的哈伯德模型模拟器,Shan 和 Mak 堆叠了二硒化钨和硫化钨层以创建莫尔超晶格,并连接电极来调节穿过 TMD 三明治的电场。电场控制着每个超级电池中填充的电子数量。由于细胞的行为就像巨大的原子,因此每个超级细胞从一个电子变成两个电子就像将氢原子晶格转变为氦原子晶格。在他们的 最初的哈伯德模型出版物 in 自然 2020 年 1.38 月,他们报告了模拟具有最多两个电子的原子;今天,他们可以增加到八个。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实现了点铅成金的古老目标。 “这就像调整化学反应,”麦说,“浏览元素周期表。”原则上,他们甚至可以想象出一个虚拟原子网格,每个原子有 XNUMX 个电子。
接下来,研究小组研究了人造原子的心脏。有了更多的电极,他们可以通过类似于向巨型合成原子中心添加正质子的改变来控制超级电池的“潜力”。原子核的电荷越多,电子就越难隧道离开,因此电场可以让它们提高或降低跳跃趋势。
麦和单对巨型原子的控制——以及哈伯德模型——已经完成。 TMD 莫尔条纹系统让他们能够召唤出一个由人造原子组成的网格,甚至是自然界中不存在的原子,并按照自己的意愿顺利地改造它们。即使对于该领域的其他研究人员来说,这种力量也近乎神奇。 “如果要我选出他们最激动人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那就是这个,”金说。
康奈尔大学研究小组很快利用他们设计的原子解决了长达 70 年的争论。问题是:如果你可以采用绝缘体并调整其原子以将其变成导电金属会怎么样?这种转变会逐渐发生还是突然发生?
Shan 和 Mak 凭借摩尔纹炼金术在实验室中进行了思想实验。首先,他们模拟了重原子,这些原子捕获了电子,从而使 TMD 超晶格表现得像绝缘体。然后他们缩小原子,削弱陷阱,直到电子能够自由跳跃,让超晶格成为导电金属。通过观察随着超晶格越来越像金属,电阻逐渐下降,他们表明这种转变并不突然。这一发现,其中 他们宣布 in 自然 去年,超晶格的电子可能能够实现一种长期寻求的流动性,即所谓的流动性。 量子自旋液体。 “这可能是人们可以解决的最有趣的问题,”麦说。
几乎在同一时间,这对夫妇幸运地获得了一些物理学家认为是他们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发现。 “这实际上完全是一场意外,”麦说。 “没人预料到会这样。”
当他们开始哈伯德模拟器研究时,研究人员使用了 TMD 三明治,其中两层上的六边形对齐,过渡金属位于过渡金属顶部,硫属化物位于硫属化物顶部。 (就在那时,他们发现了绝缘体逐渐向金属转变的过程。)然后,偶然地,他们碰巧用顶层向后堆叠的设备重复了这个实验。
和以前一样,随着电子开始跳跃,电阻开始下降。但随后它突然暴跌,跌幅如此之低,以至于研究人员怀疑莫尔条纹是否已经开始超导。然而,进一步探索,他们 测量了罕见的阻力模式 被称为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证明更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该效应表明,该器件的晶体结构迫使电子沿材料边缘的行为与中心的电子不同。在器件的中间,电子被捕获在绝缘状态。但在周边,它们朝一个方向流动——解释了超低阻力的原因。偶然间,研究人员创造了一种极其不寻常且脆弱的物质,称为陈绝缘体。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2013年首次观察到,如果温度升至百分之几开尔文以上,通常会崩溃。 2019 年,圣巴巴拉的 Young 团队在 一次性扭曲石墨烯三明治 大约 5 开尔文。现在,Shan 和 Mak 在几乎相同的温度下实现了这种效果,但在任何人都可以重新创建的无扭曲 TMD 设备中。 “我们的温度更高,但我随时都会接受他们的温度,因为他们可以连续做 10 次,”Young 说。这意味着你可以理解它“并用它来实际做某事”。
Mak 和 Shan 相信,通过一些调整,他们可以使用 TMD 莫尔材料来制造能够在 50 或 100 开尔文温度下工作的陈绝缘体。如果他们成功了,这项工作可能会带来另一种无电阻电流流动的方法——至少对于微小的“纳米线”来说,他们甚至可以在设备内的特定位置打开和关闭纳米线。
平地探索
尽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业绩不断增加,这对夫妇并没有表现出放缓的迹象。在我参观的那天,麦看到学生们正在修理一个高耸的稀释冰箱,这可以让他们将设备冷却到比他们迄今为止使用的温度低一千倍的温度。在“较温暖”的条件下有如此多的物理现象有待发现,以至于该小组还没有机会彻底搜索更深的低温领域以寻找超导性的迹象。如果超级冰箱让 TMD 超导,这将回答另一个问题,表明 铜酸盐固有的一种磁性形式 (但 TMD 中不存在)不是电子结合胶的基本成分。 “这就像杀死了理论学家长期以来真正想要杀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麦说。
他和 Shan 以及他们的团队甚至还没有开始尝试一些更时髦的 TMD。在花费数年时间发明了在二维材料大陆上移动所需的设备后,他们终于准备好冒险超越他们早在 2 年登陆的二硫化钼滩头阵地。
两位研究人员将他们的成功归功于他们在哥伦比亚大学吸收的合作文化。他们说,与 Hone 的最初合作让他们接触到了二硫化钼,这只是他们享受的众多机会之一,因为他们可以自由地追随自己的好奇心。单说,“我们不必与实验室负责人海因茨讨论”他们的计划。 “我们与其他群体的人进行了交谈。我们做了实验。我们甚至把事情包起来了。”
如今,他们在康奈尔大学营造了一个类似的轻松环境,在那里他们管理着几十名博士后、访问研究人员和学生,他们基本上都可以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情。 “学生们非常聪明,有很好的想法,”麦说。 “有时候你不想干涉。”
他们的婚姻也使他们的实验室变得独一无二。两人都学会了发挥自己的个人优势。作为一名实验者,单除了拥有丰富的创造力外,她还拥有严格的纪律,这使她成为一名优秀的管理者。当我们三个人交谈时,当“费教授”对物理学的热情让他陷入技术细节的泥沼时,她经常将他推回正轨。就麦而言,他喜欢与早期职业研究人员一起在实验室内外工作。他最近开始与团队一起攀岩。 “看起来他们的实验室就是他们的家人,”杨说。单和麦告诉我,他们一起取得的成就比单独取得的成就更多。 “一加一大于二,”麦说。
他们正在制造的设备叠加起来也可能超过其各个部件的总和。当研究人员将 TMD 片连接在一起以创建激子和莫尔超晶格时,他们推测驯化电子的新方法将如何增强技术。即使袖珍型超导性仍然难以实现,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体也可能导致超灵敏的量子传感器,并且更好地控制类陈绝缘体可以使 强大的量子计算机。这些只是显而易见的想法。材料科学的不断进步往往会带来很少有人预见到的激进应用。例如,开发晶体管的研究人员很难预测由数十亿个微型开关驱动的智能手机,这些开关被塞进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中。那些致力于制造能够在实验室工作台上传输光的玻璃纤维的科学家们无法预见到,长达 10,000 公里的海底光纤有一天会连接各大洲。二维材料可能会以类似的不可预测的方向演化。 “一个真正的新材料平台会产生自己的应用,而不是取代现有材料,”海因茨说。
在开车送我去伊萨卡巴士站时,单和麦向我讲述了他们最近(也是罕见的)去加拿大班夫度假的经历,在那里他们再次展示了通过努力和运气的结合偶然发现惊喜的技巧。他们花了几天时间试图发现一只熊,但徒劳无功。然后,在旅程结束后,在前往机场的路上,他们在一个植物保护区停下来伸展双腿,发现自己与一只黑熊面对面。
同样,对于凝聚态物理,他们的方法是一起在新的景观中漫步,看看会出现什么。 “我们没有太多的理论指导,但我们只是闲逛和做实验,”麦说。 “它可能会失败,但有时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非常意想不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