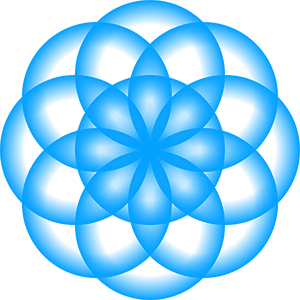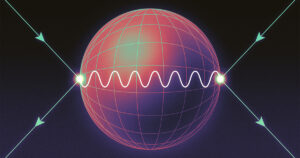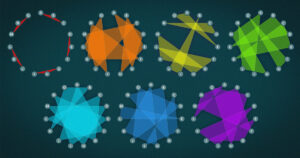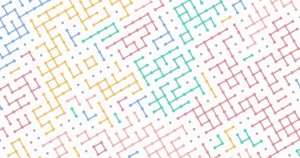介绍
在纸面上,这可能不足为奇 斯维特兰娜·吉托米尔斯卡娅,1966年出生于乌克兰哈尔科夫,成为一名数学家。 她家里的每个人——她的父母和她的哥哥——都是一体的。 她的母亲 Valentina Borok 尤其出名,因为当时她是乌克兰唯一的女性数学教授。
但她的母亲也试图警告她远离这个话题。 她认为 Jitomirskaya 没有足够的天赋成为一名研究数学家——尤其是作为一名女性,尤其是在苏联。 随着吉托米尔斯卡娅的成长,她梦想着学习俄罗斯诗歌。
由于政治和环境的原因,她只会开始从事数学职业。 在苏联,任何人文教育都难免与共产主义思想过于纠缠。 (甚至 生物学和农业科学 受到这种腐败的影响,结果是悲惨的。)数学似乎很幸福地摆脱了这一点。 因此,在 16 岁时,她前往享有盛誉的莫斯科国立大学,在那里她最终爱上了这门学科,并获得了本科和研究生学位。
1991 年完成博士学位后,她和她的物理化学家丈夫移居美国,开始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担任兼职讲师。 她迅速上前。 如今,她在欧文的头衔是杰出教授,最近她被任命为乔治亚理工学院的哈伯德讲座教授。
在她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她在分析、数学物理和动力系统问题方面的工作得到了广泛认可,今年早些时候,她被授予首届 Olga Alexandrovna Ladyzhenskaya 奖. 该奖项在与菲尔兹奖同时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宣布,旨在表彰数学物理及相关领域的开创性工作。 [编者注:2022 年的奖项由西蒙斯基金会资助,该基金会也资助了本 编辑独立杂志. 西蒙斯基金会的资助决定对我们的报道没有影响。] Jitomirskaya 的大部分研究都涉及理解所谓的准周期算子,它模拟了电子在某些环境中的行为,并与量子物理学中的各种现象相关。
她的家庭数学遗产也通过她的三个成年子女继续,他们都在追求数学事业。
广达杂志 与 Jitomirskaya 谈论了她的研究、她在前苏联作为一名年轻的犹太女性的经历,以及她对数学教育的希望。
为简化起见,访谈进行了压缩和编辑。
你的初恋不是数学,而是文学。 那是为什么?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在语言艺术方面真的很突出,而不是数学。 我喜欢写诗和读诗。 我可以读或听一首诗一两次,然后记住它。 我仍然记得数以千计的俄罗斯诗歌,都是小时候学过的。 当我 9 或 10 岁时,我的父母注意到我正在阅读他们的一份周报上的文学批评部分——他们总是会扔掉的部分。
于是我开始参加由一位著名儿童诗人领导的文学工作室。 那是我童年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一直觉得工作室帮助塑造了我的个性和我是谁。 但在批评了我的一首诗之后,我对分享我的诗变得非常害羞。 我有点没学过写作,但学会了阅读。 我学会了在诗歌中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
所以诗歌是我最深的兴趣。 我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未来的数学家。
考虑到你家里的其他人——你的父母、你的哥哥——都是数学家,这是否出乎意料?
我的一位小学老师曾经说过,我在数学方面没有那么出众,这很令人惊讶。 但实际上,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妈妈——她经常是决定这些事情的人——认为我不应该成为一名数学家。
为什么不呢?
他们非常爱我,他们想要我的幸福。 我妈妈可能认为这不是一条好路。 她所有的朋友都是数学家。 她是弗拉基米尔·德林菲尔德(Vladimir Drinfeld)的父母的朋友,这位神童在 6 岁时就可以做数学,这真的让人们大吃一惊。 [编者注:Drinfeld 于 1990 年被授予菲尔兹奖。] 她看到了一个孩子拥有数学天赋意味着什么,她没有观察到我身上的任何东西。 她可能认为我没有足够的才能获得成功——尤其是作为一个女人。
所以她非常努力地让我远离数学。 她试图引导我成为一名医生,当我很清楚我害怕看到血时,她开始给我带来心理学书籍。 但我对此不是很感兴趣。 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文学。
那么,是什么最终吸引了您进入数学领域?
我可能小时候就有数学天赋。 我不知道每个人都完全错过了它,包括我。 嗯,看着我妈妈做数学长大,我什至没有梦想我能变得像她一样。 我以为我没有它。 我不是一个很快的思考者,而她很快。 我非常钦佩她。
介绍
但现在回想起来,我确实看到了一些对数学感兴趣的早期迹象。 每一学年,当我拿到一套新的数学教科书时,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有条不紊地尝试解决所有 100 道左右的挑战性问题。 我喜欢挑战自己。 尽管我的家人很早就不鼓励我学习数学,但在数学家中成长帮助我培养了解决问题的韧性。 在家庭远足和散步时,我们最喜欢的消遣之一是解决逻辑难题。 当我妈妈提出问题时,她从不给我提示。 我记得我花了好几个星期思考这些谜题,在很多次散步后又回到同样的问题上。 即使我花了很长时间,我也会因为自己解决它而感到满足。
我决定晚一点学习数学,大约 9 年级。 我在考虑在大学学习什么。 在苏联学习语言学或文学一点也不吸引人。 它太植根于意识形态。 我不会被允许研究我喜欢的那种文学,或者研究我最喜欢的诗人,而不是每句话都赞美共产党。
我考虑向一位在爱沙尼亚工作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学习。 但他是持不同政见者,这让我父母害怕。 他们非常反对这个政权,但悄悄地反对,他们不希望我过着异见人士的生活。 所以他们说服了我。
数学是次优的。 然后我真的在大学里开始喜欢它。
这时候,你也不得不面对反犹太主义。 这对你有什么影响?
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是我的梦想。 莫斯科是一切的中心——文化的中心,博物馆的中心。 我最喜欢的诗人都在那里; 最天才的数学家都在那里。 我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动机:在我 14 岁的一个假期里,我遇到了一个来自莫斯科的男孩。 这是一见钟情——他后来成了我的丈夫。
但是申请莫斯科州立大学的机会对我来说非常不利。 他们可能会接纳一两个犹太人进入一个 500 人的班级。如果你的内部 [苏联] 护照上列出的国籍说你是犹太人,那么许多门都为你关闭了。 所以我不得不隐藏我的犹太人身份。 我的护照本应该说我是犹太人,但上面写着“乌克兰人”。 我在我的申请中谎报了我父亲的[犹太人]父名。 在大学期间,我其实很害怕它会被发现,我会被开除。
在大学期间,我也结婚了,我丈夫的名字很明显是犹太人。 我知道有这样的丈夫,我读研究生的机会为零。 所以我向所有人隐瞒了我结婚的消息,除了家人和他的朋友。 即使几年后我怀孕了,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尽管当时不结婚而怀孕被认为是可耻的。
介绍
我很难对我所有的同学隐藏它。 我大学时代的朋友都不是来自我丈夫的身边,因为我一直有这个非常大的秘密。 我无法向任何人倾诉。
你最终研究了数学物理和动力系统中的问题。 是什么吸引你来到这些领域?
事实是,在我开始研究它之前,我从不喜欢物理学。 我在物理课上做得很好,但从来没有觉得我对日常物理事件有了直观的理解。 但是当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 研究概率的导师雅科夫·西奈(Yakov Sinai)是他给我读的第一篇涉及物理学的论文。 我讨厌它。 但没有退路。 当你开始真正深入地学习一些东西,并看到一些很酷的谜团——其中一些是你帮助解开的——你怎么能抗拒呢?
你的工作如何与物理学相交?
我研究控制电子在不同材料和环境中行为的模型——例如,在有杂质的材料中,或者在 波纹材料. 尽管我研究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是纯粹的数学问题——我的一些结果涉及比宇宙寿命更大的时间尺度——但这个领域是由物理学驱动的。 物理学家不断提出需要研究的重要新兴材料,如石墨烯和其他二维材料。 人们对开发可以描述您在这些材料中看到的一些现象的模型很感兴趣。
特别是,我研究具有一些有趣的特殊结构的模型,称为准周期性。 “准周期性”是指局部看起来是周期性的[具有重复行为],但其行为在更大范围内可能看起来是混乱的。 这种特殊的结构非常适合严格的分析,您实际上可以获得我认为最漂亮的结果:您可以在更改每个参数时完整地描述模型的行为。
例如,我可能对我在几乎 Mathieu 算子上的结果感到最自豪。 该算子与垂直磁场中二维平面上电子的行为有关。 我在研究这个模型的一些显着相变方面取得了进展。
不做数学的时候,你是怎么度过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主要兴趣是抚养我的三个孩子。 我也喜欢远足、骑自行车,尤其是在大自然中游泳。 我全年都在太平洋游泳,尤其喜欢在冷水中游泳——你真的会从中获得欣快的感觉——在美丽的环境中,比如日出或日落。 我还在读诗。
你的孩子也都在学习数学。 你是希望如此,还是像你妈妈和你一样更加谨慎?
很好,但这不是我的初衷。 在他们小的时候,我亲自教他们俄罗斯文学和数学。 我想我在数学方面做得更好。 或者,也许它是内在的。 很难说。
关于教育,你也一直批评提议 数学课程的变化 在加州学校。 为什么?
我对提议的加州数学框架有很多问题,特别是它如何不强调代数和微积分,而支持所谓的数据科学,这会剥夺学生进入 STEM 专业的能力。 在所有预微积分课程中获得基本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那些想要追求 STEM 的人来说,应该有更多,而不是更少。
也就是说,我并不是说我知道如何解决美国的教育问题。 但它确实需要修复。
自从入侵乌克兰以来,你也花时间试图提供帮助。 怎么会这样?
这对每个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创伤。 两个都是我的国家。 有一段时间,我根本无法考虑其他任何事情。 从那以后,我学会了划分——数学会有所帮助,因为你往往会非常深入地参与其中而忘记其他事情。 但一开始,我什么也做不了。 三月份,我试图帮助一些朋友和他们的亲戚离开,并参与帮助从乌克兰撤离有医疗问题的人,包括大屠杀幸存者。 我还参与了为一些流离失所的数学家提供工作和教育的努力。
你什么时候离开乌克兰的?
我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就来到了美国。 1991 年从莫斯科国立大学毕业。我丈夫在加利福尼亚获得了博士后职位,我刚决定要和他一起去。 我基本上已经为任何事情做好了准备。 而且我的起点非常非常低。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兼职讲师。 一个大奖得主有这样的轨迹可能是很不寻常的。
这是否影响了您将自己视为数学家的方式?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绝对低估了自己。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的父母。 [笑.] 一方面,我从来没有因为满足他们的抱负而感到压力,因为他们对我的抱负很低。 但另一方面,它导致了一些自尊问题。 我认为我实际上比他们对我的看法更好,也比我对自己的看法更好。
另一件事是,起初,我并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研究生。 尽管我在本科时表现出色,但在开始研究后的头几年,我只是没有结果。 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的导师给了我非常棘手的问题。 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辍学。 但不知何故,我有继续下去的韧性,我实际上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 共有七篇论文。
此外,也许我起步如此之低的事实导致了我自己部门的一些严重的尊重问题,尽管得到了外界的认可,但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失。
然后,每次我得到一些认可时,我都会怀疑我得到了认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很不爽。 如果他们不亲自了解女性的研究,并且听说她获得了一些奖项,他们肯定是因为她的性别。
你什么时候开始有不同的想法?
它是逐渐发生的。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不,我应该得到认可,无论我的性别如何。 也许我的性别在某些方面有所帮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应该得到它。 但直到最近我才对这件事形成了一种更健康的态度。